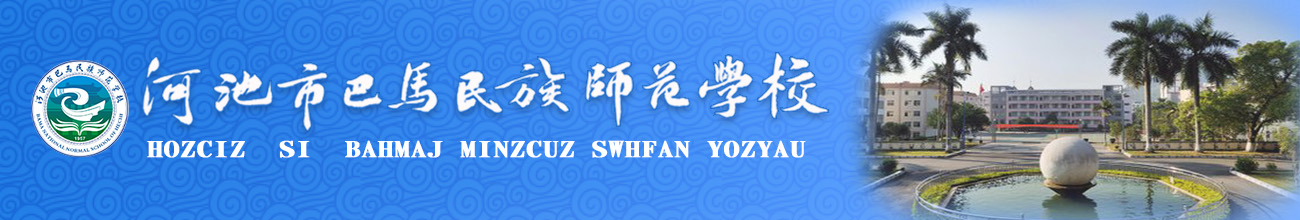1999年,我从巴马民族师范学校毕业后,分配到龙滩水电站上游红水河畔,天峨与贵州罗甸交界处的豪明村完小任教。在这深山里,一呆,就呆了10多年。期间,因为交通不方便,我一直没有机会回母校看过,也没有见过母校的任何一个老师。
直到2009年5月12日上午,河池市“三项教育”巡回活动报告团到天峨作巡回报告。头晚,学校通知我参加报告会的时候,我就听说,市里请了一位著名学者来作报告。那天早上,因为下雨,街上很拥堵,我迟到了几分钟才赶到人民会堂。当我步履匆匆进到会场找地方坐定之后,抬头间,令我意想不到的是,坐在主席台上作报告的,竟是我日夜牵念的恩师,罗伏龙先生。整个上午,我都在兴奋和激动的状态中,听完报告。
散会后,我跑到后台找到先生,紧紧握住他的手,不肯松开,甚至喜极而泣。多年不见,先生依然健朗。虽然年过花甲,但仍风度翩翩,不减当年。除了略显疲惫外,丝毫没有衰老的样子。那时,他已卸去校长的职务。是的,先生太累了,他该歇歇了。见到他,我的记忆,一下子,又飘回那青涩的学生时代。
其实,我和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,是和先生的引导分不开的。
刚进师范的第一个学期,我压根就不懂什么叫文学。不过,倒听说过,学校有一位著名作家、诗人和学者叫做罗伏龙。当时,我们几个懵懂少年,相约加入文学社的初心,纯粹是因为看见文学社的学长们,看起来,特别像文化人,以为这些文化人最有优越感。每天放完晚学后,不论在亭台楼阁里高谈阔论,还是在草坪上吟诗作对,都能引来路过女生的一片崇拜的目光。
1997年的秋天,学校《桃李园》文学社,邀请罗伏龙先生来讲课。就在这次文学创作讲座上,我第一次真正认识了罗伏龙先生。先生给我的印象是,潇洒的中等个头,举止温文尔雅,讲话出口成章,瘦弱的身体充满了书生气息,很有魅力。也在这次讲座上,我第一次认识了文学。
记得,讲课结束后,文学社安排学员们,到学校后面松山里参观碑林。碑林是学校的文化名片,它收集展览了学校历届师生的优秀书画、诗词和文学作品。
在攀登松山的时候,偶然间,有一段路,我和先生并肩而行。先生边走边和蔼的问我说:“你叫什么名字呀?是哪个班级的?喜欢写作吗?”
看见他脸上始终挂着和蔼的笑容,是那般温和亲切,完全没有想象中高高在上的样子。
我一下没了心理压力,于是把自己的姓名和所在班级都告诉了他。
先生听后,爽朗的笑着说:“原来你是96级7班的呀?那可是特长班哟!个个都是才子咧!以后,如果你在写作上遇到什么困难,可以找我,我一定尽力帮助你。”
在谈到写作技巧时,先生告诉我,写作是没有秘诀的,写得多了,就能摸出个道儿来;初学写作的人,不要有意去模仿别人,一开始就要形成自己的模式;要多看书,阅读是写作的基础,看的多了,就能看到别人写作的长处,同时,也能看出自己的不足,通过比较就能博采众长,才能步步提高。
一路上,我们谈笑风生,交流了许多关于写作的话题。先生的一席话,让我增长了见识,也让我清晰认识自己在写作道上的误区。就这样,我有幸和先生相识,并成为了朋友。
时隔多日,我带一篇自认为很满意的作品去拜见先生。他在办公室,热情接待了我。他很认真的阅读我的作品,然后对我说:“你写的文章总体上还可以,有骨也有肉,只是初学写作的人有一个通病,就是对细节的描写把握不够,喜欢叙述,这样,文章就显得苍白空洞。好文章不但要有骨有肉,还要积累丰富的生活阅历和情感经历,写作跟做人一样,要有真情实感,才能打动人,感染人。如果只靠瞎编乱造,就写不出好文章来。加油,相信你能行。”
和先生的这次谈话,虽然时间很短,却让我受益终身。他的教导让我深受启发,不但让我对写作产生更浓厚的兴趣,还教会我为人之道。
在先生的鼓励下,我鼓起勇气给一些刊物投了稿件。一天,我忽然收到《河池教育》编辑部的一封信,心情既激动,又不安。然后,迫不及待的拆开信封,里面有一本《河池教育》杂志。我欣喜若狂的翻找,终于看见生平发表的的第一篇散文《心灵憩息的净土》。晚上,我捧着那本书,反复看了一遍又一遍,睡不着觉。
后来,我的作品陆续在不同的刊物发表,越来越多。还有幸成为作家群里的一员,创作的平台更加广阔。
回首走来的一路,与其说《桃李园》文学社是书香文苑,不如说巴马师范是我文学创作的成长起点,罗伏龙先生更是我的启蒙老师。
他那严谨的治学态度,渊博的学识,淡泊名利和对事业执着追求的精神,对我的一生,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以至于后来,我也成为一名人民教师之后,仍坚定朝他所走的方向努力奔跑!
很庆幸成为罗伏龙老师的学生。